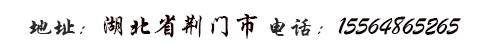葫芦河年4期马骏微小说二题
|
白癜风有哪些要忌 https://m-mip.39.net/nk/mipso_5878257.html文学之乡——西吉《葫芦河》精品选读 通向文学高原的驿站寄托美丽乡愁的载体 全方位展示“中国首个文学之乡——西吉”文学发展现状,全方位展示西吉作家诗人风采,全方位培养文学新人,推出文学精品力作。 微小说二题 作者:马骏 一百元夏天摸了摸自己的裤兜,就是这张舒展的人民币,也只剩一张一百块了,一百块能干什么呢?夏天想了想。可他又不想开口向家里人要。索性,到捐献箱前把这一百块塞进去,然后离开。可旁边有工作人员看见了,拍照的拍照,采访的采访。 有人描绘着:大雪纷飞的一天,有一个轮椅少年,他名叫夏天,带着口罩,看不清他清秀的面庞,他左手搬动着轮椅的操控杆,在雪中小心翼翼地掌握着方向,右手拿着一张崭新的一百块钱,在寒冷中打着哆嗦。狂风怒吼,雨雪交加,夏天艰难的来到了捐献箱前,将这一百块钱投了进去,这是在雪中送炭啊。 采访的人热泪盈眶的看着夏天,说:“孩子,你真是身残志坚,冒着大雪来为武汉捐献这一百元。你有什么想法?” 夏天激动的说:“我为武汉加油。” 采访者又接着说:“你没有想想,这可是你每天捡饮料瓶赚来的钱啊。” 夏天平复了一下心情说:“虽然我残疾,但我也要献出自己的一份爱。” 采访者继续说到:“你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,我为你骄傲,我们会把这个故事写下来,让更多人知道的。” 是否如此?这个故事真是这样吗?其实,故事是一传十,十传百。一下子,夏天捐款的事儿传到了好多地方,大家都认识了一个叫夏天的轮椅少年,他冒着大雪,为武汉捐献一百元的故事。 夏天很苦恼,他也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做了这样伟大的事儿。自己怎样就身残志坚了?夏天对身残志坚的含义有些模糊,这个词不应该是拿来炫耀的。他的好朋友尤意也知道了这事儿,便联系到夏天,想知道详细的情况来为他写一篇文章,这可是个好故事啊,从事自媒体行业的尤意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。 当尤意从夏天那里得知详情后,有些失望,他真希望前面那个故事是真的。那日,夏天看新闻,武汉突发新型冠状病毒,好多医务人员都去支援武汉,白衣天使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病人医治。他想到了自己,自己也是让白衣天使救过来的。他们就是夏天的救命恩人,此时,恩人有难,他不能就这样静静地坐着,可他坐着轮椅又能帮什么忙呢? 下午时候,他看见公众募捐活动,便带了口罩,坐着自己的电动轮椅,出去了。夏天本来不想出去,自己从生病以来几乎没有收入,他看着天花板,想着该去哪里找钱呢?没钱捐赠,可他内心又好强,又不愿向家里人索要,因为那不是他自己赚来的钱。他突然想到,床底下还有一百元,上面还标着三个“8”呢,是他健康的时候压在床底下的。他本想,白衣天使们也不缺那一百元,不捐也罢。可他看着新闻联播里的一幅幅画面,总发呆。夏天眼前医院的那段时光。倘若不是那些可爱的天使们,他也许活不到今天。只有床底下那一百元属于自己,一百就一百吧,他准备趁人不注意塞进募捐箱就匆匆离开。这样也不会有人知道他只捐了一百元。此时,夏天看了看天空,蔚蓝的天空里有一朵云,云朵就像那白衣天使们甜美的微笑。天气是暖和的,因而夏天才有坐轮椅的环境,大雪纷飞是不适合坐着轮椅出来的。 来到募捐现场,大家都特别忙,没有人注意到坐着轮椅的夏天是来募捐的,大家也想不到他是来募捐的。好多募捐的人都排在前面,夏天根本排不上队。夏天在后面转悠过来转悠过去,有个拿着照相机的人,一直盯着夏天看。恰巧有一个志愿者从夏天面前走过,夏天喊住了这个登记的志愿者,把一百元递给她说:“阿姨,请帮我把这一百元捐给武汉的白衣天使们。” 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 “还要说名字啊?” “对啊,是要登记一下的。” “我叫夏天。” 话还没有说完,又有很多捐献的人员前来,大家都绕过夏天,挤在前面,夏天坐着轮椅,多多少少有些挡道。他趁着工作者忙碌时候,便匆匆离开。就在离开的时候,有个拿着相机的人,他问夏天叫什么名字?来干什么?夏天说了名字和为什么来这里。说完,慢慢操控轮椅离开了。那个拿着照相机的男子就拍下了夏天离开的背影。 土豆中秋佳节,回到久别的故乡,蓝天下的泥土气息扑鼻而来,我看着夕阳下仅有的一丝余晖,深吸一口气,走进门,闻到烧土豆的味道,这味道突然把我带回了几十年前。 夜色不知不觉降临,几个玩伴偷出家里的柴火,来到人迹稀少的山坡边,挖一个土坑,侧边在挖一个灶火洞,土灶之上用泥土疙瘩围住,架上柴火,拿来自家地里的土豆,点起火种。通红的带点蓝色的火焰在轻柔的风中飘舞身姿,半蹲在篝火旁的玩伴们从厚实而不取暖的皮袄袖子里哆嗦着伸出手,把土豆放在火上烤着。周边的其他玩伴相互取笑,你推我一下,我也不服气地搡你一下。你拿起土疙瘩吓唬我,我拽住你的脖领叫你来打。不知不觉,土豆的香气钻入了每个人的鼻孔,大家都停下手头的事儿,用冻僵的手试探的去抓外表已经烧糊的土豆。 一把将土豆抓过来,摔在冰冷的地上,此时也许是被刚烤熟的土豆烫着了,触动身体的感触器官,鼻孔里那不争气的鼻涕速溜溜流下来,举起手,用手指骨节按准鼻子,快速一捋,鼻涕就止住了。然后拿起土豆,再使劲摔在地上,打掉土豆上面的焦皮,馋嘴的伙伴快要流下哈喇子了。伸出通红的手,将土豆一掰两半,那刚出炉的热气再次灼烧着手指,不由自主地丢下土豆,把手放在耳边去摸摸通红的耳朵。那钻鼻的香气让哈喇子在嘴边回荡,动作快的玩伴迅速拿起土豆,用被土豆焦皮、泥土,还有不争气的鼻涕弄脏的手去剥掉干皮儿,顺着热气边吹边咬下去,然后崛起嘴唇将土豆吸进嘴里,那真是色香味俱全,一点都不在意土豆上沾染了什么。 “你看你那蠢样儿,看把你烫了。” “你有本事你来啊,自己不敢动手拿热洋芋,还说别人。” “赶快吃,不然一会爹找来了。” …… 谁会在乎大哥所说的话,大家还是相互吵闹着、大笑着、玩闹着,你说一句,我抬一句杠。 一溜烟时间,土豆也不再那么烫手。你吃我也吃,玩伴们都相继拿起手边的土豆,“狗蹲子”蹲在那里,粗略的剥掉皮,开心的吃起来。其中的味道,只有吃了的人才知道。篝火依旧亮着,冷风依旧吹着,通红的手拿着热腾腾的土豆,你吃一个,我吃一个。天是冷的,人却没有感觉一点冷,冷被热闹、开心欢乐裹挟走了,再冷的天,也冰封不住那蹲在一起相互嘟囔的热情。土豆的香气夹杂着这欢闹声,在九月天的冷气中飘满村头。 一晃哥几个都长大了。昏暗的白炽灯亮着。一个不太大的屋子,里面坐着一家人,大伯二伯、大婶二婶、表哥表姐、表弟表妹,热闹非凡。外面的风依旧在怒吼,大家都不愿出去,屋里有炉子,炉子上架着一口大锅,锅里有洋芋,一家人都挤在炕上,说着家常,谈着琐事。 “爹,咱家今年不挨冻了,往年哪来这么多柴火。” “日子慢慢好了,咱也不挨饿,不受冻了。” “爷你胡子长了,我给你拔了吧。” “别瞎闹,快下来,那是你爷留了多年的胡子。” “没事,叫娃玩,娃没有见过白胡子。” 炉子里的火渐渐熄灭,锅里的香味渐渐入鼻,娘离开炕头,拿下大锅,揭开锅盖,那种味道,闻着就忍不住流下哈喇子。娘又从炕上赶下顽皮的孩子,在炕头摆上桌子,长辈坐在上席,晚辈们坐在炕边,大家都盘腿坐下,桌上摆着一大锅土豆,中间放着一大碗腌制成的韭菜。锅里的洋芋上没有焦皮,只有那细细的一层皮儿。剥开土豆细细的皮儿,拿筷子夹上韭菜放在洋芋上,大口咬下去,淀粉的酥、滑、润填满整个口腔,边吃边聊。炕头很热,炉火很热,土豆吃在嘴里,热在心头。 哥几个也都成为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也有成为爷爷的,家里的黑白电视变成了彩电,电视里面再也没有“雪花儿”,看着就和真人在面前一样。那泥泞的道路也一去不复返,曾经零星看见几辆自行车过往,现在柏油马路上一辆辆高级小轿车数不清数儿,再也不见三八大梁车了。 还记得当初哥几个在离开那熟悉的村庄时的场景。有几个身体高瘦,穿着大麻布织的衣服,手里拿着一个花布织成的手提包,后面背着被一个大床单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被子,在父母的送别下,离开了自己的家乡。唯有小弟弟在家里,照料那几亩农田。 兄弟几个出去后,也没有回家的时间,家里的乡亲也不允许回家,几个青涩少年也没有了回家的念想,只盼啥时候有颜面回家。 多年过去,小屋子已经变成了大房子,华丽的吊顶灯照亮了宽敞舒适的房子,里面没有了炉子的篝火,地暖提供了所有热度,一个人独坐在沙发上,等待着厨房里电磁炉上的洋芋,期待着它的香味,看了看周边,没有人能陪着聊聊天。打开手机,翻阅着朋友圈的动态,给长久不能相见的朋友点着赞,电视取代了家人的欢笑声、伙伴的打闹声以及姐妹的吵闹声。自己只低着头看着手机,任电视把吵闹声传遍房子中的每个角落。 不知不觉,土豆已经烧好了,将土豆摆在茶几上,旁边放着各种味道的榨菜,期待着多年前吃土豆的香味回来,用干净的手掰开土豆,剥掉皮儿,土豆上没有一点土,放上各种榨菜,闭上眼睛回味多年前吃土豆的模样,大口咬下去,却没有了那美好的味道,那种欢声笑语下的味道,那种泥土飘香的味道,那种韭菜的咸味。 吃在嘴里,仔细品味,拿起手中的一半土豆,仔细看着,是不是现在的土豆都是高科技种植的新品种,没有了以前的味儿呢?不,不是。是不是榨菜不好呢?不,也不是。是不是自己的味觉下降了呢?不,也不是。那是什么呢?土豆的味道去哪了呢? 土豆的香味留在了荒野的山头边,那里太寒冷,这香味在那里可以缓解冷气。土豆的香味留在了土炕头,那里需要这香气夹杂韭菜。土豆的香被高高围起的宏伟建筑阻挡在了外边。 我们把自己的家修建得富丽堂皇,把自己的事业也干得风生水起,然而我们的家里少了一些人。打电话叫来忙碌的家人,公司里少了大儿子的一桩会议,游戏厅里的游戏机停了一台,少了小儿子的身影。电影院的电影票少了女儿与对象的两张影票。华丽的灯光下不再是一个我和一盘没有香味的土豆,欢笑声压住了液晶电视的节目声。 看着一个个开心的脸庞,拿起土豆,忘记了放榨菜,一口咬下去,似乎尝到了以前的味道。但还是不满足,还是感觉没有吃够。 第二天早晨,一早告别媳妇,孩子。坐上飞机,几经周转,最后一站是班车。在班车上,看见了久违的蓝天,看见了蓝天下麦秆在风的摆动下排练的精彩舞蹈,是那么整齐,又是那么优雅,这不,有几个拿着农具的乡亲在指挥这场舞会。经过几个小时,终于来到了村头,这次没有告诉小弟,偷偷来到这里,徐步走在乡间小路上,一切都是新面孔,那茅草屋,还有土木房子都不见了踪影,村头有一幢别墅似的二层洋楼,楼下是高高的铁门代替了木门,门口停着一辆四环车。继续往村里边走,家家都是这样的水泥房子,晚辈们也一个都不认识,长辈们也不见了踪影,只有周围的那一丛丛麦秆还似曾相识。 走着走着,看见了一个穿着红背心,身体黝黑壮硕的中年男子正在田间忙碌着。我没有说话,只是慢慢向他走去。他转过身来,看见了我,先是一愣,然后就开心地笑了,向我迎面跑来,大声喊着:“哥。” 一个带着眼镜,脸面光泽明亮,手拿公文包,穿着一身黑色西装,后面拉着行李箱的中年男子站在一个脸上留着整齐胡子,穿着红色背心,手拿锄头,肤色黝黑的中年男子面前。西装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。弟弟想拥抱我,却上下打量着我,迟迟不敢上前。我主动迎上去,我俩相互拥抱了一下。 “哥,你咋来了,这都多少年没有回家了,回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。” “我只是想回家看看,看看咱家怎么样了,看看你还好吗。” “这不,还是老样子,家里啥都没有变。” “不,变了,啥都变了。” “俺没有感觉,好像还是那样。” 说着,两个人一同回家。刚进门,就看见小侄子和弟媳妇一起忙着晚饭,没错,正是那土豆的香味。 “媳妇,你看谁来了。”弟弟喊着。 弟媳妇急忙走出来,开心地说:“原来是,大哥,快进屋。” 屋里有几个孩子,他们都来向我问好。弟媳妇端来了土豆,说:“哥,这是刚煮熟的土豆,你可能吃不惯,先将就一下,冰箱里还有肉,我去给你做点饭。” “不用,不用,这土豆刚刚好,我爱吃着呢。” 还是炕头,不过这次我和弟弟坐在了上席,弟媳妇和孩子们坐在炕头,我拿起土豆,一瞬间,那久违的土豆香味,又回来了。 《葫芦河》 huluhe 文章原载:《葫芦河》年第4期 监审:樊文举 编审:李义 编辑:马世梅 主办:西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敬请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tumuxianga.com/tmxyyy/6325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州3027云南省文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