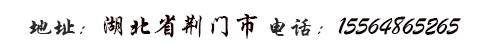散文王学信算黄算割,杜鹃声声麦子黄
|
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正规 https://yyk.39.net/hospital/89ac7_knowledges.html 作者:王学信 (摄影:DavidClode) “算黄算割”、“算黄算割”……四声杜鹃鸟的高声鸣叫,拉开了拂晓那张灰黑色的大幕,东方天际由鱼肚白而光亮、由光亮而淡红、由淡红而托起一轮红红的火球,冉冉东升。我聆听着杜鹃鸟高唱,看着清晨瑰丽的阳光,深切感受到“龙口夺食”的“三夏生产”,又一次匆匆而至我的“农耕文化”的故乡。 母亲摸黑就起床了,精心熬好了苞谷糁糖,用油炝好了自己“窝”的酸菜,看看天不早了,轻声叫醒了赖床的我。我揉了揉惺松的睡眼,一骨碌势起身。母亲昨天晚上,已作了农事安排,今天收割地里边角拐弯的麦子,以便迎接收割机莅临作业。 母亲原本是不让我下地的,说这活她完全能干,往年都是她一个人干的。还说,她年轻的时候,夏收时和父亲、爷爷一起割麦子,“面向黄土背朝天”,左手抓住麦子上半部,右手挥镰割下半部,尽量割得低一些,麦茬留得越低越是“好把式”;她一天也能割半亩地呢!哪一年实在忙不过来了,便去新筑镇“集”上,掏钱请“麦客子”来割。这些“麦客子”一般都是从南山里出来打工的男子汉,因了山里小麦收割晚,他们打“时间差”,先来平川“赶集”挣钱,平川麦子收完了,自家麦子也黄了,再回山里收割。这些人身强体壮,浑身是劲,一个人一天轻轻松松割一亩多地。母亲则给“麦客子”做饭,擀她拿手的“燃面”。这些人很能吃,一顿吃三大碗“燃面”,还要再用油泼辣子夹一个馍吃。母亲说,社会发展得很快,科学也很发达,后来研究出收割机,把人从劳累中“解放”出来了,夏收再也无须弯腰躬背、汗流浃背地苦干了。只需“割”一下地边边的麦子就行了,这算个啥活呢,跟耍着一样!我说我专门从城里回来收麦子,总不能言而无信“放空炮”吧?母亲见我一缠二磨的,犟不过我,便答应带上我上地。 我起床后,草草洗漱了一下,便走进厨房,立马就被苞谷的清香、酸菜的油香,勾起幼年味蕾的记忆,顿时馋涎欲滴,欲罢不能,不由分说,便端起大老碗呼噜呼噜地咥了起来……母亲又舀了一老碗糁糁给我晾着,自己则铲锅底,吃略有点焦灼的“咎咎”(锅巴)。她边吃边一脸伤悲地喃喃自语:村里开始征地拆迁了,以后再也吃不到自己种的新鲜粮食了,唉…… 我家这里要修建“全运会”场馆,拆迁好几个村子呢,我们小村也在其列。母亲倒是有全局意识,能配合拆迁;但故乡情深,恋恋不舍,心里就像打碎了五味瓶子,很不舒服,时不时便唠叨几句。 吃罢早饭,大约9点了,太阳一杆子高了,露出红扑扑的圆脸蛋,该去我家那块充满灵气的麦田干活了。母亲取出两把她早已磨好了刃片的长柄镰刀和两顶草帽,让我拿着。她则提了一热水瓶开水、带了两个小搪瓷碗,准备中途干累了的时候休息解渴。 走出村头,便见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色麦浪迤逦翻滚,就像黄河的波涛一样蛮有气势;阵阵麦香扑鼻,翩翩蜂蝶起舞,绿树红萏,鸟语花香,让人神清气爽,悠然自得。但也有办了拆迁手续的乡党,房子被拆得“残垣断壁”,与金黄色的天地很不协调。 我家有二亩多小麦地——是当年父母亲的承包地,位于阔大的阡陌之一隅,长势还算不错。麦杆半人多高、麦穗三四寸长,从上到下,通体橙黄橙黄的,已经熟透了;风儿一吹,“摇头晃脑”,舞动身躯,喜孜孜地欢迎人的青睐。说实话,看着一派生机盎然的麦地,我还真的不忍心对她动“手术”。我们必须动的“手术”,便是割掉麦地周边的麦子,撒向留给收割机作业的麦子顶部,让收割机“代为”脱粒。 (摄影:OlgaDivnaya) 我家麦地的北边畔上,栽着一溜花椒树,是土地承包到户那年,父亲栽的。他专门去了一趟南山,买来优质花椒树苗。这些年来,有的椒苗已长得碗口粗细、两人多高;一般的也跟胳膊一样粗、一人多高了,都在盛果期,枝头挂满了一爪一爪颗粒饱满的花椒。椒树高处阳光充足,花椒外皮已呈现红色,绿叶红椒相映点缀,缕缕香气空中飞飘,煞是可心喜人。但这也带来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——“歇地”,影响小麦生长。椒树下一米多宽的小麦,都长得很孱弱,杆矮穗瘪精气不足,好像噘着嘴埋怨:花椒树呀,你们以强凌弱、以大欺小,太不仗义了吧! 而且,由于椒树枝繁叶茂,笼罩空间,收割机很难靠近,必须人工割掉这一米多宽的麦子,均匀地铺撒,让收割机一道脱粒。地的东西南三个边界,没栽花椒树,只需割掉一尺左右即可,也让收割机“代劳”。如果不这样劳作,收割机因了躯体庞大,转弯调头之际,便在地边留下一溜割不倒的麦子。此时,人工补割倒也可以,但脱粒就很难肠(困难)了。不如让收割机一起处理,卷入机仓自动脱粒,非常方便省事。 自然,我和母亲先从北边割起,那时母亲已年近九十,因了长期在乡村劳作,身体还硬朗,步履也矫健。她摊开需要割掉的一多半麦子,挥镰如飞,嚓嚓嚓,一割一长溜;我也是“古稀”龄了,紧跟母亲后边,割另外那一小半。我们母子俩,一个银发飘飘,一个霜发黢黢,倒也是一道风景。割一阵子,回首看麦子茬口处,只见闪露出紫红色的刺荆花和绿莹莹的野生小香蒜,很是让人欣喜眼馋。 红日当空,气温越来越高,我和母亲汗流浃背,气喘吁吁。好在已经割到地头了,得歇一口气。 地头东北角是父亲的坟墓,父亲安卧此处已经十多年了;坟墓东北地边各留有两米左右空地,以便“机耕机种机收”时,机车方便转弯调头。这里自然也得割倒一圈小麦,以免收割机碰撞坟体。母亲很小心翼翼地割着,生怕惊醒了睡眠中的父亲。往年,只割最外边一尺许,但这回母亲让全都割掉,不让收割机拐进来了,包括坟堆上零零星星长着的麦子,也割得干干净净,坟墓周围顿时清爽起来。母亲说,公家马上征地呢,再没有下一回”了,让你大(父亲)也知道这事吧。 清理完父亲坟墓周围的麦子之后,我和母亲坐在坟头休息。母亲给一个搪瓷碗倒满开水,端起,倒入另一个搪瓷碗内,俩碗来回倒了几次,开水便不烫嘴了。她让我先喝,我让她先喝,推让之中,母亲脸上又浮起明显的伤感,眼角也湿漉漉的。她终于忍不住了,擦了擦眼泪说,娃呀!往年割了麦子,接着就种苞谷,还要在地头靠水道的地方留出半分来地,栽冬葱,种箩卜白菜等大路菜,一冬天也吃不完。今年全都成了泡影了,啥也不能种了,唉…… 休息了一会,母亲带着对土地的深深眷恋,继续埋头干活。边干边念叨,我本是土里生土里长的黄土地老婆子,快入土了,却要离开黄土地,跟你进城,去住钢筋水泥大楼。城里的活,我啥都不会干,也没啥事可做,往后日子怎么打发呢?咋想咋都不接地气,唉…… 我赶紧说,妈呀您都九十高龄了,干了一辈子活,受了一辈子苦,把儿女一个一个养大,贡献委实不小,还想干啥呢?您进城后,想吃就吃,想睡就睡;太阳出来暖洋洋,我陪您去公园闲逛,尽享清福;熏风吹来气候爽,娃们与您一起玩耍,享受天伦之乐,欢度晚年…… 干到中午一点多,四个地边都割清爽了,天也大热了。我和母亲上衣都被汗水湿透了,该收工回家吃中午饭了。 我们疲备地回到家里,我要动手做饭,母亲却坚决不让。她似乎有使不完的劲,很快洗了手,轻车驾熟地淘菜、合面,炒菜、擀面,不大一会儿,就麻利地做好了“燃面”。饭后,我让母亲歇着,自己则在已拆迁的乡党的房舍外,捡了半架子车碎砖块,拉到地头垫水道,以便收割机顺利进地,不受绊磕。 可是,等了两三天,每天拂晓,四声杜鹃都“算黄算割”“算黄算割”嘹亮而竭力地高唱,提醒乡党抓紧收割,不误农时,但却硬是叫不来收割机。据说,司机嫌这片麦地的道路难走,拆迁了的乡党,门口堆着拆下来的水泥板,很难通过;而且这一片麦地面积较小,仅有三四十亩,挣钱少,划不着来收割。 眼看眼麦子黄透了,有的颗粒都掉到地上了。母亲看见圆圆的、黄黄的、饱滿的麦粒脱落在地,心疼不已,闹着要自己拿镰刀去收割。我说,妈呀您老糊涂了,割了以后怎么脱粒呢?一无场地可晒,二无碌碡可碾,反倒是大麻烦呀!母亲只好“唉、唉”着作罢。但她家里——地里;地里——家里,出出进进,坐卧不宁。无奈,我只得冒昧给包村干部打电话,恳请助农纾困。包村干部还算负责任,与“拆迁组”商量之后,疏通了道路,又高价雇了一台收割机,总算把这片小麦全都收割了。我把我家的小麦拉回家晾晒清理,母亲则戴上草帽,提个竹笼子,拿一把苕帚,去地里捡拾落下的麦穗和收割机轮胎压倒的麦子。她一穗一穗地仔细捡拾,一处一处地认真清扫,尽心尽力地“颗粒归仓”……然后,她提回家晾晒、捶打、揉搓、用簸箕搧得干干净净,装入粮食口袋。自然,她也不会忘记摘几竹笼尚未成熟的花椒,说以后连这低档的花椒都吃不到了,唉……我则找了一个塑料袋,装了几抔黄土,留作诀别故乡的纪念。 别了,可爱的“算黄算割”;别了,故乡灵杰的土地;别了,美丽的家园;别了,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老屋……我倒是“四海为家”惯了,心态还算坦然;但母亲却是一脸的惆怅和恋恋不舍。 年11月20日 (原文标题:《别了,“算黄算割”》 (摄影:rajeevramdas) 作者简介 王学信,笔名灞柳。本是西安市灞桥区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,弱冠之年,离家外出求学,异地工作,乡情乡愁满腹。闲暇喜欢读书思索,提笔蘸墨,时有作品见诸报刊网络。 壹点号一点写作课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: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,或搜索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tumuxianga.com/tmxjb/1165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故事女子和男闺蜜喝酒,次日清晨被送回家,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